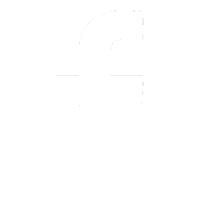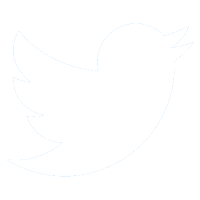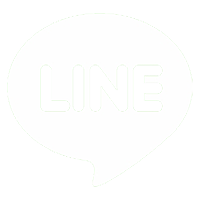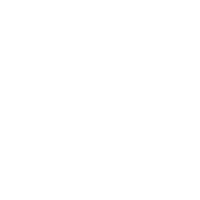帶心率監測的耳機,並非蘋果首創。
過去十年,Jabra、Sennheiser、Beats 都在這條賽道上嘗試,但這些錦上添花的功能都沒能打動 Nick Harris-Fry,作為資深跑者、Tom’s Guide 的健身編輯,他幾乎試遍了所有品牌的心率耳機,結論卻始終一致:沒有一副耳機能與胸帶的精度相提並論。
胸帶,那條勒在胸口略顯不便的裝置,至今仍是普通消費者能買到的最可靠的心率監測設備。
直到 AirPods Pro 3 的出現。
Nick Harris-Fry 以 Garmin HRM600 胸帶(電信號級精度)作為對照,結果發現 AirPods Pro 3 的心率曲線幾乎與胸帶重合,尤其在穩態跑與間歇跑這種對精度要求極高的場景下,兩條曲線如同鏡像般貼合。

更令人驚訝的是,它能在播放音樂的同時,感知你的心跳頻率、判斷步伐節奏,並實時識別超過 50 種運動類型。
AirPods Pro 3 是如何實現的?
為了找到答案,專訪了蘋果感知與連接副總裁 Ron Huang 與健康感知總監 Steve Waydo,在這場對話中,我們試圖理解的不僅是一項新技術的工作原理,更是蘋果如何思考「身體」這個終極界面。
耳道,也許比手腕更懂你
從生理結構上看,耳道是一塊天然的傳感「黃金地帶」。它靠近顳淺動脈,血流灌注穩定,又被外耳包裹,幾乎沒有外界光線干擾。
這些特性,讓耳道成為比手腕更理想的生理信號採集點。

美國一篇論文《可穿戴光電容積脈搏波分析原理及其在生理監測中的應用》明確指出:
耳道 PPG(光電容積描記)信號在血管分布、抗運動干擾和環境光抑制方面,優於腕部與指端。
相比之下,手腕是一個充滿變數的測量場域。肌肉頻繁運動,擺臂幅度劇烈,汗液、毛髮乃至膚色都會干擾光信號的傳播。
蘋果健康感知總監 Steve Waydo 在實驗中反覆驗證了這一點:在力量訓練、划船等需要握緊器械的場景下,腕部設備往往難以穩定測心率,而耳機測到的血流信號更加連貫。

在耳道這個暗箱式環境中,AirPods Pro 3 採用了紅外光 PPG(IR PPG) 方案————有別於市面上大多數設備使用的綠色 LED 光源。
Steve Waydo 解釋說,紅外光的能耗更低,也避免了「耳朵冒綠光」的尷尬。
更重要的考量是,紅外波長更長,穿透力更強,能夠深入血管密集的耳道組織,捕捉到更乾淨、更穩定的脈衝信號。
AirPods Pro 3 的傳感器每秒脈衝約 250–256 次紅外光,同時結合 IMU(加速度計與陀螺儀) 數據,用來消除運動偽影——比如跑步時腳步觸地帶來的節奏性震動,或者轉頭時產生的加速度變化。
這種光學信號與動態數據融合的算法,是 AirPods Pro 3 能在運動中保持心率精度的關鍵。它不是單一傳感器的勝利,而是多模態數據協同的結果。
蘋果感知與連接副總裁 Ron Huang 補充說:
當用戶同時佩戴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Pro 3 時,系統會在最近 5 分鐘的信號里滾動比較,並自動選擇更可靠的來源。
例如在力量訓練中,手部抓握動作較多,腕部設備的數據會受到干擾,系統就會更多優先選擇來自耳道的心率信號。
從這個角度看,Apple Watch 和 AirPods Pro 並不是為了相互取代,而是為了在不同場景下互為補充,共同在為同一個身體建立更完整更真實的數字鏡像。
十年算法的縮小成果
Waydo 的團隊從 Apple Watch 誕生之初就開始積累算法。那套神經網路原本是為手腕設計的,針對的是腕部血管的光學特性、手臂擺動的運動模式、皮膚組織的光散射規律。
但令人意外的是,這十年的積累並未因平台切換而作廢——它們成為了 AirPods 心率傳感器開發的基
由於耳機的空間極為有限,AirPods Pro 3 使用的是 Apple Watch 心率算法的「小型化版本」。
他們從原型耳機中採集到的大量數據,進一步微調模型,使其在極端條件下也能準確追蹤心率。測試包括不同膚色、耳型、溫濕度和運動強度,甚至在寒冷氣候中仍保持穩定。
「貼合度」是在採訪中被反覆提到的一個關鍵詞,它不僅關乎聲學體驗——主動降噪的效果、空間音頻的沉浸感,更直接決定了生理數據的準確性。
當耳塞貼合良好時,雙耳協同的心率讀數非常精準。
Steve Waydo 說。
這也是蘋果在 AirPods Pro 3 上重新設計入耳結構、優化矽膠耳塞形狀、升級自適應調音算法的隱性原因——那些看似為了聲音的改進,同時也在為生理監測鋪路。
像大語言模型那樣:如何讓耳機理解 50 種動作?

準確的心率監測只是起點。
蘋果的目標是:讓 AirPods Prio 具備與 Apple Watch 相當的運動體驗——不僅要知道你的心跳快慢,還要理解你正在做什麼運動,消耗了多少卡路里,跑了多遠的距離。
這意味著,蘋果必須榨乾「所能利用的每一個傳感器。」
AirPods Pro 3 在感知系統上其實是像個「小生態系統」。在耳機側,它部署了加速度計、陀螺儀和心率傳感器,在 iPhone 側,則貢獻了 GPS 與氣壓計。這些傳感器產生的數據流,需要被實時整合、解析、轉化為有意義的運動指標。
Ron Huang 提到,Apple Watch 上已積累了大量動作信號的經驗,比如跑步時手臂的擺動、划船機訓練的動作模式等。把這套能力遷移到 AirPods 後,需要把原來針對手腕的動作觀測「翻譯」為對頭部運動的觀測。
為此,團隊借鑑了大語言模型(LLM)的訓練思路——通過海量數據學習通用的「動作語法」,而非為每種運動硬編碼規則。
他們基於 Apple Heart and Movement Study(心臟與運動研究)中約 5000 萬小時的真實運動數據,訓練了一個全新的動作基礎模型(Motion Foundation Model)。
那是一項蘋果幾年前面向公眾發起的開放研究,參與者自願捐獻來自 Apple Watch 與 iPhone 的運動數據。
它本質上是一個回歸模型,能理解你在做哪些活動、是否在對抗阻力、動用大肌群還是小肌群、運動平面與身體姿態等。
為了確保算法能覆蓋普拉提、HIIT、橢圓機等不同類型的鍛煉,蘋果邀請了不同體能與技能水平的參與者進行測試與校準。
在實驗室中:他們採用了被認為是「黃金標準」的方式——佩戴氧氣面罩,用代謝面罩(Metabolic Cart)觀測真實氧氣交換率,以驗證卡路里模型的準確性。
在步數與距離的追蹤上,團隊開發了全新的行人運動神經網路。他們邀請數百人進入生物力學實驗室,使用標定跑步機記錄距離,在鞋底放置壓力傳感器標記落腳與離地時刻,並用攝像機捕捉完整步態。
最終,他們得以在 AirPods 上「一次性推出超過 50 種運動類型」的追蹤能力,而這在 Apple Watch 時代花了幾年才達成。
從聲學到身體:技術的終極歸宿
作為一種時刻貼近身體的設備,AirPods 天然地處於一個微妙的位置:它既面向外部世界,放大聲音、過濾噪音、重構空間,又面向內在自我,感知呼吸、追蹤脈搏。
當一個聲學器件開始理解心跳的起伏、步伐的韻律、身體的語言,它就不再僅僅是一個輸出設備,而是一個雙向的感知界面。
從「聽世界的聲音」到「聽身體的聲音」,這條路徑延續了蘋果一貫的產品哲學——技術最終要回歸人的感知。
耳機曾經只是音樂的出口,內容的播放器。而現在,它正成為身體的入口,自我認知的傳感器。當技術學會傾聽身體,它才真正學會了傾聽人。
何宗丞 (Jonathan Ho)
從技術的旁觀者與記錄者,成為技術影響生活方式的實踐者。
郵箱 Twitter Flickr Google 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