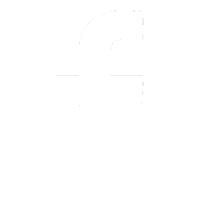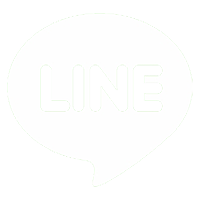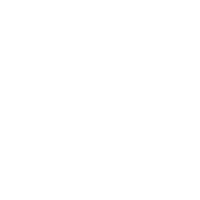我只希望能夠在某個瞬間觸碰到永恆,在那個完美的瞬間儘量感受,當萬物都恰到好處,世界也與我融為一體。

2007年,漫畫家坂本真一以昭和時期登山家加藤文太郎的經歷為藍本,創作了不朽的青年漫畫《孤高之人》。

簡單來說,那是一個有關於山與人的故事。主角森文太郎被描繪成一個不顧一切痴迷登山的怪人,他極端沉默寡言,被周圍的人視為異類,不求財富,不在乎家庭,把全部的精力、金錢、執念聚焦於登山。在社會的洪流里,他只是一粒沉沒水底微不足道的泥沙;但當山矗立在眼前,他總會選擇獨自攀登,不依賴任何隊友,又比任何人爬得更高更遠。

有些人,生來就是要攀登的,山是他唯一的朋友。肉體與山岩碰撞,與風的律動同頻,似角馬遷徙,像大雁南飛,被社會麻痹的感官被重新激活和放大。但它們是基因為了生存的最優解,而攀登只是為了攀登,是人對於達成某種極限的渴望,在那個完美的瞬間與世界融為一體的感受。攀登是不同的,只是聽從本能,一心向上飛。

上個月底剛發售的登山生存遊戲《孤山獨影》,就是一款遊戲版本的《孤高之人》。遊戲發售5天時間,已經在Steam上拿到超過5000條評價、94%的好評率。僅限於好評率最為苛刻的國區,這個數字也有86%。
製作組TheGameBakers並非無名小組,之前也有《Furi》和《Haven》兩款特別好評的作品。尤其後者是一個極美的作品,講述一對情侶為了彼此,放棄一切私奔到一座失落的星球,關乎愛、抗爭、與自由。

但《孤山獨影》仍然是特別的,它不像是為玩家做的,更像是為了遊戲本身,為了登山而做的。從沒有一款攀岩模擬遊戲像它這般真實,真實到讓人「痛苦」。它會讓你產生極致的耐心和專注,你需要在漫長的數小時攀登的每一秒、每一毫秒內,都保持極致的注意力。任何懈怠換來的,可能都是受傷、跌落和死亡,因為山不會保護你,山不會在乎你,山只是在那裡。

但也從來沒有一款攀岩模擬遊戲,像它這般具有代入感,能輕而易舉讓你進入心流狀態。千仞雪山崩潰於眼前,獵獵風聲躍然耳邊。主角的心跳、呼吸、愉悅、痛苦,無時無刻不會順著手柄和耳機,傳入你的指尖和肌肉。你不在山上,但心中自有一座神山。諸種心象的繪畫如履薄冰,偏又化險為夷。
阿爾卑斯式登山,是一種登山者以自給自足的方式,即自己攜帶少量裝備、物資去攀登中高海拔山峰。因為是阿爾卑斯山區登山運動的早期活動形式,所以以此命名。當時歐洲登山界的主流看法是:阿爾卑斯式攀登更加貼近現代登山運動的精神本質,並且不會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。
儘管經常被冠以「賽博鰲太線」之名,但《孤山獨影》其實與鰲太線代表的「徒步」,和剛爬上101大樓的Alex Honnold代表的「徒手攀岩」都不太一樣,而是像《孤高之人》的故事那樣,是典型的阿爾卑斯式登山,一種融合了徒步、徒手攀岩和荒野求生的,難度極高的綜合性戶外極限運動。

遊戲中的你,是一位攀岩界內頗負盛名的女性攀岩大師「艾瓦」。征服諸多山峰之後,她向著被無數人挑戰過,但從未有人成功登頂過的神之山「卡米峰」發起了挑戰。

背上包,帶著有限的食物、水、醫療品和輔助工具,一路利用周邊環境滿足所有生存需求,然後攀上山頂,這就是遊戲的全部。
其實故事也沒有主動交代你的任何背景資訊,登山不需要這些,只需要往更高更遠處前進。大師也好菜鳥也罷,攀登都是一種風險行為,而不是技巧表演。你並不會因為熟練就變得安全,只是學會了更謹慎地做出決定。甚至於知道自己是攀岩大師,還是因為在神山上偶然遇到的迷弟。但這都不重要,登山不需要這些。

無論是世界第一的徒手攀岩大師Alex Honnold,還是征服了K2喬戈里峰的《孤高之人》男主森文太郎,都和常人無異長著雙手雙腳,你也只能用雙手雙腳登頂卡米峰。《孤山獨影》真實感的核心,在於它構建了一套極為擬真,且充滿張力的「肢體管理」系統。玩家需要像親自攀岩那般,獨立控制登山者艾瓦的雙手與雙腳,去尋找岩壁上的支點。

手腳與岩壁接觸時的摩擦聲清晰而克制,每一次抓握、每一次發力都會切實地消耗體力,並通過角色的四肢顫抖和痛苦的喘息直觀地傳遞給你。隨著高度上升,風聲逐漸增強,周圍的聲音變得稀薄,世界仿佛只剩下山體與攀登者自身。大自然沒有文字,但痛苦和聲音,能讓你更清晰地感知到自身的存在。

徒手攀岩是世界上最危險的運動之一,歷史上幾乎所有頂尖的徒手攀岩者最終都會墜亡。這一運動追求的是力量與體重的最佳比率、耐力以及對抗肌群的平衡。手指與前臂力量是攀岩的第一道門檻,需要能長時間抓握小邊緣,因此耐力比絕對力量更加重要;背部肌肉完成引體、側拉等動作的關鍵;核心力量則能維持整個軀幹的穩定性。不容忽視的還有腿部和臀部力量,因為在陡峭岩壁上,雙腳承載了大部分體重。強大的腿部力量能讓你不可思議地站在岩峰之間,而不是靠手臂苦苦支撐。

所以,你需要比任何人都清楚,你正在做的是一件什麼樣的事情。除非撿到前人留下的地圖,否則《孤山獨影》都沒有預設的攀爬路線,需要讓你自主觀察山體的情況、牆面的複雜程度、落腳點與著力點的分布等等要素來勘探路線,選擇適合自己的。這是一件融合了路線規劃、資源管理與風險決策的複合冒險。

現實中Alex Honnold在徒手攀登一條路線前,會進行無數次的有繩練習,記憶每一個手點、腳點、身體移動順序、休息位置。他也會把路線「模塊化」和「序列化」,在腦中形成一個精確的攀登程序,直到整個過程像走路一樣成為肌肉記憶。

山是唯物的存在,它沒有靈魂,不保護、不在乎,也不懲罰任何人,一切情感寄託都是人類的一廂情願,或者說是人類內心意志的寫照。登頂只是人類算計出一個最安全的時間與環境路線,配合體能的結果,若因此認為自己戰勝了山,只是自欺欺人罷了。
《孤山獨影》便是用這種方式,讓你意識到登山的本質。在不開輔助模式的情況下,遊戲只會在露營地存檔,跌落山崖便意味著從存檔點重新來過。你會反思是不是自己的注意力不夠集中,或者路線選擇有問題。於是你學會了充分利用每一樣道具,滑石粉可以增加手部摩擦力,有限的岩釘是你的臨時存檔點,即使跌落也能救你一命,讓你沿著繩子輕鬆爬回原來的位置。

想要登頂神之山,絕不是幾天的事情。你會口渴,會飢餓,會失溫,會受傷,以及需要睡眠。你首先是一個需要營養的有機生命體,你需要活下去。
遊戲將這種生存博弈,凝練為背包中有限的格位與篝火旁簡單的烹飪。清水與草藥化為藥湯,凍魚與牛奶在鍋中翻滾。一餐精心組合的食物,帶來的除了卡路里,還有爆發力增益或寒冷抗性,這可能就是在下一段絕壁上生與死的差值。

高強度的摩擦,會不可避免地對手指造成磨損傷害。藥物、繃帶的地位也和飲食對等,不可或缺。

生存的瑣碎與攀登的崇高不得不交織在一起。你悉心照料這具肉體,這具會顫抖疲憊,渴望溫暖的凡軀,以觸碰唯有摒除一切雜念才能窺見的永恆。山不在乎你是否飽足,但你的每一次吞咽與安眠,都是為了下一次,能將雙手更穩地交給岩石。

閱讀《孤高之人》,會對一個人所能承受的苦難感到錯愕。文太郎所遇之善無善終,所遇之惡不勝數,連唯一的朋友大西老師也面目全非死在山上。他自責只要事情和他扯上關係,就會變得一團糟,於是社會屬性被完全掩埋,他成了孤獨的怪物,只有山不在乎他是什麼人,社會賦予他所有不合群的異類標籤,都在絕對的孤獨與危險中剝落殆盡。

但他對山的追求,令人深深敬佩,甚至是毛骨悚然。獨攀的孤獨和痛苦,對他來說是崇高的救贖與恢復之路。即使是死,也要死在攀山路上,死在曠無人煙里,死在登頂的希望與絕望中。

有一種剝離了空間和時間的、生活在鋼鐵叢林中的人無法看到的美。

《孤山獨影》所呈現的,同樣是那種註定孤獨,但不惜一切的生命狀態。主角選擇登山,沒有理由,更不為了名利,而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,熱愛、嚮往、困惑、迴避、痛苦、執念混雜的複雜和矛盾。
這種矛盾,沒有被包裝成英雄主義。你不是一個性格討喜的人,甚至不是尋常意義的探險家。你控制不住地發怒、焦慮,對夥伴辛苦拉攏的商業投資人愛答不理。你是一個剝離者,主動剝去社會身份、人際牽絆,乃至對意義的追問。登山對你而言,更像是在確認,確認剔除所有噪音之後,那個僅憑本能向上的生命體,是否還算存在。

於是,山的故事成了你與孤獨的對話。你見過日照金山時岩壁流淌的熔金,也曾在暴風雪裹挾的白色黑暗中,憑觸覺分辨前進的方向。

你會注意到前人的屍骸、鏽蝕的岩釘,像閱讀一段無言的墓志銘;也會在某個向陽的岩縫裡,發現一株顫抖的、不合時宜的花。

脫離鋼筋混泥土的庇佑,你會從暴雨和雷電中感受到無法平息的盛怒,但有時你也必須前進,直到下一個能稱得上露營地的地方,在孤獨和恐懼中,捲縮在帳篷里熬過這一夜。

但在閃電風暴過後,一定是那充滿藍天白雲,充滿碧草繁花的世界。

所有這些體驗,其實都無法透過文字、圖片以及影片完全分享。它們只是發生,然後沉澱為你的骨骼與記憶。但最終,所有這些激烈的情緒都會被山的龐大與恆常吸收,凝結成平靜。你會漸漸學會用它的語言,用夜、空、雪、風和岩石重新拼湊自己。

當世界被簡化為下一個支點,那種與萬物融為一體的永恆瞬間反而會不期而至。不僅僅是自然環境提供的,更多來自選擇本身。當你選擇向上的時候,你也在一步步遠離很多人。
登山是一種極致極端的選擇,但現實里許多人也在選擇不被主流敘事認可的道路:創作、研究,或某種與社會晉升渠道脫節的生活方式。從經濟利益的角度,這樣的選擇不夠理性;在家族責任方面,甚至會被指責自私;但對自己而言,那是感受自身存在價值的唯一渠道。
遊戲沒有通過直接的劇情來表達任何價值觀,而是讓攀登過程本身承擔敘事功能。神山並非絕對的無人之境,海拔不高的區域頗受攀登愛好者的青睞。你能找到早年攀登者搭建的避風港和簡陋餐吧的遺蹟,岩洞裡甚至殘留著狂歡節的彩帶與永不消逝的搖滾樂回聲。官方修建的鏽蝕索道支架,指向一個這裡曾作為觀光地存在的、已模糊的過去。這是山被人類」馴服」或「享用」的邊緣,充滿了練習、交流與煙火氣的痕跡。

這裡沒截圖,借用一下UP主鳩木采的素材
神山也有自己的人類史,大量碎片化的故事被安排在洞穴與遺蹟中。歷史上曾有一群信仰神山的人在此建立了近乎自足的村落,他們被稱為「穴居人」。岩壁上開鑿的農田、深入洞穴的養殖池、用於傳授知識與攀登技巧的學校遺址,以及莊嚴的聖所與成年儀考驗場……他們耕種、捕獵、繁衍、崇拜、埋葬,形成了一個圍繞山峰建立的完整文化閉環。

你不知道他們是何時消亡的,只能作為後來者,孤獨地穿越他們曾生活的地方,發現他們留下過的印記。
攀登路上,你也會遇到一些「當下」的青年留下的打卡印記,看著他們隨著年齡增長,一步步爬到神山更高更遠的地方。但是從來沒有人登頂過這座山,所以你知道他們最終都死去了。


這些印記證明了人與山互動的可能性,也如同沉默的路標,最終將你選擇的這條孤獨的道路,映照得愈發清晰而極致。
1885年,時年20歲的美國青年Wilson Bentley成為了史上首位「真正看見」雪花的人。他後來成為氣象學家,畢生拍攝超過五千張雪花照片,發現沒有一片是相同的形狀。

Wilson只是美國佛蒙特州的一個農場小孩,在那個年代想拍攝雪花需要付出極為困難的成本和代價,但也讓他獨一無二,讓他第一個親眼目睹了雪之華。

正如開頭所說,《孤山獨影》不像是為玩家做的,更像是為了遊戲本身,為了登山而做的,和Alex Honnol、森文太郎、Wilson Bentley和遊戲主角艾瓦一樣,在追求極致的路上前進。

以工業化的遊戲設計標準去評價《孤山獨影》,它在很多方面都「不太合群」。節奏緩慢、弱引導、負反饋強烈,雖然有設計大量人性化的輔助功能,但官方卻並不推薦你使用。因為所有非技術力相關的「缺陷」,就是刻意為之,是有意把判斷的權力交給玩家,讓你像一位真正的登山者,攀爬很久之後再回頭望去,無法置信自己究竟已經走過了多少路,完成了多麼了不起的壯舉。

(強劇透預警)
《孤山獨影》的最後,為你提供了兩個結局。在卡米峰的「刀鋒區域」,你會遇到此前結識的,另一位經驗豐富的登山者馬爾科,他明白神山的危險,也懂得何時該放棄。若選擇和馬爾科一同下山,你迎回的是人間的暖意——篝火、朋友、以及一位始終等待你的愛人。結尾動畫會以溫柔的筆觸素描你們攜手歸途的風景,仿佛為這場苦旅畫上一個體面的句號。

這是明智的生存抉擇。然而「歸家」成就的英文名「Those who come back down」(那些下山的人),本身就帶著一絲微妙的疏離感。你活下來了,但眼神中的空洞,卻提示著某種失敗。

承認世界上存在不可逾越之物,並與執念和解,或許需要更大的勇氣。
而選擇繼續向上,則將回扣遊戲開場「觸碰永恆」的渴望。在頂峰衝刺的路上,艾瓦遭遇了一場猛烈的雪崩。在很多玩家看來,艾瓦的生命其實就在這裡戛然而止。肉體被無盡的白色吞沒,現實的攀登於此畫上休止符。
但遊戲不會在這裡結束。帶著體力減半、補給銳減、消耗速度大幅加快的多重Debuff,艾瓦最終成功登頂,她站在山巔發出了勝利的吶喊,然後,開始攀登星辰,仿佛與天空、與神山融為一體。

這是遊戲的第二個結局成就「Part of a Whole」,「融為一體」。你永遠成為了山的一部分,以一種絕對的、永恆不朽的方式,念天地之悠悠,獨愴然而涕下。

森文太郎最終是幸福的,艾瓦也是,也許螢幕前的你也一樣。怪物的標籤被山風撕去,只留下一個純粹的靈魂,與一座純粹的山。山重塑了你們,就像它重塑了曾經穴居的村民、隕落的前輩,以及身處鋼鐵叢林中,仍渴望攀登的自由靈魂。

最終,遊戲本身也成為了這樣一座山,而攀登過這座山的人,或許都已在某個瞬間觸碰到了自己的永恆。那片永恆不在於是否真正登頂,而是在於你也曾真切的、孤獨的、全然的活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