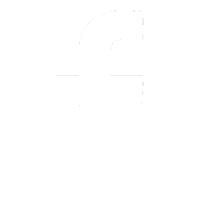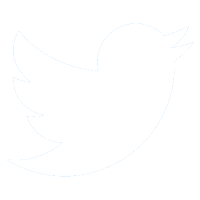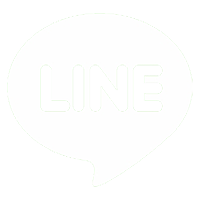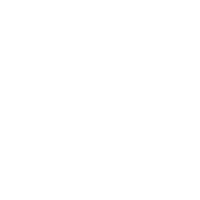周末的舊金山黃昏,許多人悠閒享受一日裡最後的陽光,但 28 歲的 AI 初創公司創始人 Marty Kausas 依然待在辦公室里忙碌著——「不然還能在哪兒呢?」。
這位創始人在領英上曬出帖子,自己連續三周每周工作 92 小時,戰績可查。
Kausas 的故事並非特例。在當下的矽谷 AI 創業圈,這種睡在辦公室的極端創業現象正變得普遍。一批 20 多歲的年輕創始人幾乎廢掉了周末,奉行著「不喝酒、不睡覺、不社交」的準則,誓把全部清醒時間投入工作。

他們不是在 OpenAI、Gemini 這樣的巨輪上,而是自己打造了一艘小船,就衝進了席捲世界的 AI 浪潮里。
沒有天價的工資年包,拿到的投資款可能還沒頂級研究員們一年的工資高,但他們的決心,比任何人都強烈。
只要干不死,就往死里干
當工作成為唯一的生活重心,這些年輕創始人甚至將最基本的睡眠和休息也安排在辦公室里。
在他們的世界裡,辦公室不僅是工作場所,更是餐廳、客廳和臥室——有些創業者就在工位旁打地鋪,或乾脆睡在會議室的沙發下;還有人乾脆租下類似於日本膠囊飯店的「睡眠艙」。

想像一下,一排排像棺材一樣的小盒子整齊擺放,拉上帘子就是漆黑一片。
AI 聊天機器人創業者 Haseab Ullah 每月花 700 美元住這種共享空間,和 20 來個同道中人做鄰居。他自嘲說:「每晚躺進去都感覺像躺進了棺材。」——這話聽著扎心,但也夠真實。
睡覺都能湊合,吃飯就更不講究了。為了省時間不分心,有人一天就吃一頓外賣,有人直接靠代餐和各種補充劑續命。傳統意義上的娛樂?那是什麼,能吃嗎?

這群人不去 party,不泡酒吧,連行業聚會都很少見到酒精。風投公司 Headline 的活動策劃 Michelle Fang 發現,很多 AI 創業者的聚會壓根不提供酒水。
一來,在舊金山這個圈子裡,喝酒早就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事兒;二來,更直接的原因是——相當多創始人才十八九歲,法定飲酒年齡都沒到呢。
睡在辦公室,吃飯只為活命,這還是那個動不動就「整頓職場」的 00 後嗎?畫風轉變得有點猛啊。
繁榮巨浪的背面
表面上看,矽谷仿佛又回到了移動網際網路時期、風雲變幻的創業浪潮中。但熱潮背後,商業邏輯和競爭壓力,才是真正讓人食難安、寢難眠的現實。
首先是資本的潮汐:在生成式 AI 掀起浪潮的近兩年裡,創業融資經歷了過山車般的起伏。2023 年全球私營領域對 AI 創業公司的投資總額約為 960 億美元,比 2022 年的 1034 億略有下降——總體上降溫了近 20%。

資金分配也出現了有趣的結構性變化:拿到融資的 AI 初創公司數量不減反增。根據斯坦福大學的 HAI 報告,2023 年宣布獲得融資的 AI 初創企業多達 1812 家,較前一年激增 40.6%。也就是說,湧入賽道的玩家越來越多,但單筆平均融資額在縮水。
這一方面說明 AI 創業門檻降低、百花齊放,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錢難拿了:除非有超強的硬核實力,現在很難再出現動輒上億美金融資的神話。

即便拿到了錢,也不意味著前途一片光明。典型例子是 Stability AI 公司:這家主打開源 AI 模型的明星創業公司 2022 年底估值一度超過 10 億美元,但據報道其 2023 年營收卻只有區區 1100 萬美元,而經營支出高達 1.53 億美元。
換句話說,這一行,燒錢遠快於賺錢,商業前景未必能支撐起先前的天價估值。資本再有錢也會學乖,不能再靠想像中的指數級增長來硬撐估值,AI 賽道需要更加理性和紮實的發展節奏。

在此背景下,行業競爭的「卷度」之強可想而知。同質化競爭已經成為 AI 創業圈的隱患。很多初創團隊都是依賴「套殼」來回來去就是幾個基礎模型,包裝出不同的應用。
誰能率先跑馬圈地、拿到用戶和收入,才有機會殺出重圍。也難怪風險投資人感嘆,現在已經沒胃口資助一堆缺乏差異化的新玩家。大家更願意把子彈留給已經占據制高點的大模型公司,或者那些有明確壁壘的垂直應用,虹吸效應初現,進一步刺激內卷。
要名,要利,要成為勝利者
在這麼艱難的環境裡,這幫年輕人為什麼還要前仆後繼地往火坑裡跳?是什麼讓他們把自己逼到這種程度?
理想、幻想,還有赤裸裸的名利慾望,交織成了最真實的答案。

對財富和成功的渴望,在創業圈從來都是最強的興奮劑。「財務自由」「獨角獸神話」這些故事,一茬接一茬地激勵著後來者。
今天的 AI 創業熱潮,活脫脫就是上世紀 90 年代末網際網路泡沫的翻版。當年那些車庫創業者憧憬著一夜暴富、上市套現,現在 AI 就是那張可能改變命運的彩票。
有人坦言:「創業者這麼拼,無非是想儘快賺到改變人生的錢。沒人希望一直 996 干到 65 歲,他們要的是早點實現財務自由。」
於是,AI 的浪潮被看作是「21 世紀的淘金熱」,甘願放棄大公司的高薪和安逸跑去創業——只要賭贏這一把,回報將是天文數字級別的。

這種近乎執念的逐利心理,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創業投資體制的強化。VC 們習慣押注那些「all in」的創始人——凡是肯拼命、睡地板、連續作戰的創業者,往往被視為有激情有韌性的優質標的,這種導向無形中鼓勵了極端奮鬥文化的蔓延。
可除了為名為利之外,還有一種深層的緊迫感——對時代洪流的「fomo」,fear of missing out。

人工智慧技術在近年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,從 GPT-4 到各類新模型疊代不過幾個月時間。技術曲線陡峭攀升,巨頭林立,留給小團隊的窗口期稍縱即逝。
許多創業者都有種共識:「千載難逢」的機會就在眼前,不抓住就再也沒有了。Y Combinator 合伙人 Jared Friedman 觀察當下景象,不禁感慨「歷史正在重演」——眼前這些充滿幹勁的年輕人,讓他仿佛回到了網際網路萌芽時期,那時 PayPal 等公司里員工也曾睡在工位下熬夜苦幹。

不同的是,這次 AI 浪潮的規模可能是當年的十倍,有望孕育出下一個蘋果、谷歌式的偉大公司。可是另一方面,競爭之激烈、演變之迅猛也前所未有。面對這種節奏,這些 20 出頭的創業者,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:技術方案變數重重、市場反饋稍縱即逝、資金鍊緊繃……每一項都可能讓心態崩潰。
這些創業者拼命追求的,不僅是工作回報,更是在爭奪一種面向未來的話語權:AI 時代的勝利者身份。
更魔幻的是,這些創業者不僅自己投身 AI 創業,連他們的第一批「員工」都可能是 AI:各種 agent、模型、chatbot。項目原型靠生成,代碼用 AI 寫,設計讓 AI 出初稿再去 Figma 調整。

AI 工具讓創業變簡單了嗎?或許吧,但也讓自我剝削變得更容易了。
—個人的精力和韌性、團隊的凝聚和文化、資本的耐心和算計,所有的這些要素都會在時間長河中被驗證成敗。一腔孤勇可以創造偉業,但也不是沒可能黃粱一夢。
也許再過若干年回頭看今天,我們會發現那些真正存活下來的 AI 巨頭,並不一定來自最瘋狂內卷的那撥人,相反能夠走遠的恰恰是張弛有度、穩健前行的團隊。
但無論如何,這群當下晝夜不舍的年輕創業者,已經在 AI 浪潮的篇章里留下了獨特的一筆。他們的堅持和掙扎值得被記錄和關懷。
在快速奔跑的技術進步面前,有時候仍然需要一些自我提醒:再熾熱的創業夢,也應允許有停下來喘口氣的時候。